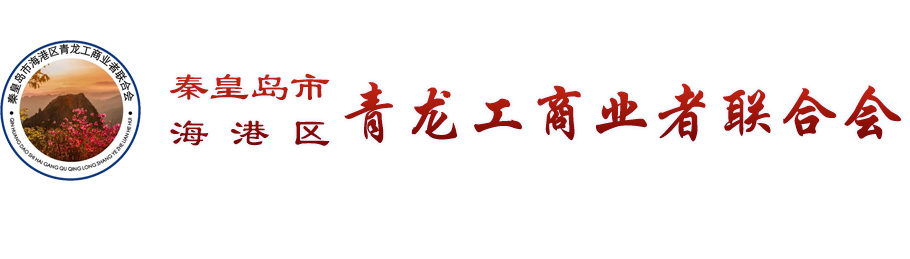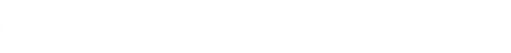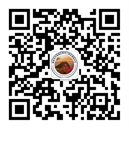龙年的春节回老家青龙县城,恰逢开放烟花燃放,除夕之夜,甩掉鸡肋的春晚节目,走上久别的山城小镇,为的是追寻儿时的光影,圆圆孩提的美梦。
夜幕降临,我信步街头,震耳的声音传过来,顿时一组组烟花射入夜空。那绽放的五光十色焰火,照亮了街市狭窄胡同,点红了市民的笑脸。不间断的炸响,此起彼伏的闪光,冲入耳膜,闯入眼帘。
听!清清脆脆的是二踢脚;噼里啪啦的是挂鞭;唱着华彩乐段冲入夜空的是“黄鹂”;叫声格外悠扬婉转是“百灵”。它们在呼唤着春的清新与秋的繁荣。看!“钻天猴”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不刺青天不罢休;“旱天雷”一声惊炸震天宇 ,催落春雨洒人间。那火树银花夜空里,有牡丹的货贵,秋菊的高雅,冬梅的傲骨,迎春的轻盈,有散花天女的潇洒,还有动物王国的顽皮,它们因物象形,各具特色,群星世界如此晶莹璀璨。啊,我实在叫不出众多爆竹的名字,也无法比喻美不胜收的焰火。爆竹声中我的心在激荡,烟花光里,我的眼泪悄然流淌……。
如梦如歌如泣如诉的童年——关于爆竹的故事,又一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
小的时候,我和北方农村家乡顽童一样,十分盼望过年,盼望什么?一是能吃几顿猪肉解馋,再就是放爆竹。往往从正月初五就掰指头计算:“再过十一个月零二十五天又过年喽”。
我们那个地方,给二踢脚叫高升,挂鞭叫响鞭,当时多为这两种爆竹。
进入冬季,小男孩们便积攒一点破布头、碎骨头、旧鞋帮卖到代销店,为的是换上几分钢蹦,买高升、响鞭。没有这些“废品”,只好眼巴巴地等着。我的伙伴秋头,攒了半筐碎铁、碎布,让妈妈换了盐,他哭了半天。另一个伙伴九头,因为和妈妈要钱买爆竹,挨了两火棍子,他妈的理由是:“别人放高升,你还不一样能听响吗”?
买上高升、响鞭的孩子就成了“王”,神气的把脑袋摇成拨浪鼓;没买上的就求情:“等放的时候叫我一声哦啊”。
那年月,高升论根卖,有时响鞭拆挂论个卖,因为大家都没钱多买。谁家买上成挂的鞭,或者一圈为一百根的高升,那可是半庄人都喝喊、羡慕。我们家境还是可以,每年都能买上十几根高升和一挂响鞭,因此,在同伴的眼里我最富有,当然也就最神气、有资本。可妈妈经常瞪我说:“那玩意是赶穷气用的,得放到点子上”。听妈的指点,我把那几根高升排好日期:腊月二十三是小年,庆贺一年生活不坏放一根;除夕吃接神饭放三根;初一早上大吉大利放三根;初五放一根是有祸必破;十五元宵节,廿五添仓各放一根;再就是二月二龙抬头放一根。就这么十来根高升,断断续续放了一个多月。我放高升就担心点不着或者响一节。点不着怕不吉利,响一节怕第二节崩远了被人抢走。每次两节都响了,心里特别顺畅,否则,心里窝屈半天。不到放鞭炮的日子,心里痒刷刷的,总要翻出来摆弄摆弄,一旦过了爆竹的“瘾”,心里又有几多失落:没了……。
我们都珍惜初一的早晨放鞭炮的时刻,这阵子可以多放一些,还可以炫耀。每逢这时,我家门口都少不了冻得起鸡皮疙瘩的九头;袄大身小用绳子捆腰的三头;耷拉帽衫,偷一个油糕换三个响鞭的秋头;还有石头、东头、生头……。我放鞭炮的方法是高升、响鞭一齐点,还要找个水桶,桶口朝上对着挂鞭,为的是响声大,没响的能掉在水桶里。一阵“噼里啪啦——叮当”过后,伙伴们蹦高拍巴掌:“真得!”。接着一双双冻红的小手,伸向了碎纸堆,划拉来划拉去,可望找几个臭屁股的响鞭。
我永远忘不了可怜的伙伴石头,他弟兄五个人排行老大,妈妈瘫痪,爸爸疯狂家暴虐待。在我的记忆中,他从来没有过属于自己的高升和响鞭,但他是看爆竹的好“观众”,听响声的好“听众”。每到春节,他起得最早,家门串得最多,他成个冬天没戴过帽子,耳轮冻出紫泡,脚上的胶皮车轱辘底子鞋,探出两个脚趾,走起路来擦、擦、擦地响。他常年流鼻涕,鼻孔下冲出两条白道道,嘴唇时不时地抿一抿,惹得大家扭皱鼻子。他手上的皴老厚,象干裂的松树皮。他穿着肥大的免裆裤,裆前挂着白渍尿斑,走两步拎一拎。但他人好,干活手头快,打柴时经常帮助别人,所以很和群。有一次他围观放高升,第一根响了一节,让这“松树皮”抢去了;第二根“咚”的一声响了,刚落地又被“松树皮”撩住了,“当”第二节响了,鲜血从“松树皮”上流出来,他皱下眉头,从破袖子上扯下一把棉絮裹了裹流血的手,拣起爆裂的高升筒子,“擦、擦、擦”地又和大伙玩去了。那年正月十五放高升,大家望着石头,左等也不来,右等也不来。原来,石头家境破败,生活无着,前一天他把自己栓在一棵梨树上上吊了。摆弄尸首时,人们发现他不闭双眼,叔伯们说:“这是石头穷家难舍啊。”婶娘们说:“石头惦记他瘫在炕上的妈”。我说:“石头是没有舒心地放过一回爆竹而不瞑目……”
高升、响鞭是伙伴们的宝贝,也是资本。平时一起玩耍,相互闹了别扭,鞭炮就成了揭短的把炳。
“那我放高升,你还去看?”
“那我放高升,你也听响了?”
“等我再放高升,谁再敢去看着?”
直到对方不敢吭声了。
有个女孩叫巧英,她大姐结婚过门那天放高升,她把我们堵在胡同里不让看。我们几个央告给她一条红头绳,她还是不放行,嘴里嘟囔着:“谁看我们放高升,生疔长疮”。我们只好攀着墙沿,掂着脚,遥望他哥放高升。春节到了,她乱麻般的头发扎了一条红发带,到我家门口看热闹,我以牙还牙撵走了她,她自知理亏,只好躲在一棵柳树后面,露出红发带,用耳朵欣赏了我的高升。响声过了老一阵子,“红发带”才敢转过身来。
伙伴当中,我的点子较多,经常挑动别人把手中的高升放了,留下我自己的。九头的亲友捎来五根高升,我把他骗到公路边,讲吊高炮(平放)怎么怎么好,他听入了迷,真的吊了一根。我又把他带到洞下面哄他顶着桥顶放,说能顶上去顶下来好几回,他受骗了,白搭一根。事后听说因为这两根高升,他妈骂了他,以后一见面,九头让我赔他高升,吓得我直躲。
时光荏苒,日月如梭。如今我们都步入了老年了,秋头耍木匠,九头开汽车,生头开商店,我在广电当记者退休。我们的孩子们和孩子的孩子,也都会放爆竹了。他们买爆竹用的皮包、麻袋、手推车、三轮车……有圆的、有扁的、方的、长的、会飞的、会叫的、闪光的、冒烟的,什么“响天雷、“宝葫芦”、“鸣天叫”、“百鸟飞”、“枊絮飞花”、“吉庆有余”……真是名目繁多,数不胜数。
人群中,我碰上了多年不见的九头,他不声不响地甩给我一盒中华烟。我问他:“九头,今年买多少烟花爆竹?”
他说:“那还有数?大概得这个”?他伸出两个指头。
我说:“二百元?”
“不,是两千元。拉了一三码车。咳,咱们那阵子,两毛呗……也不用想。要是石还活着……”我急忙捺了一下九头的肩膀,止住了他的话头,对视了一眼,各自走了。
追忆着这不夜山城的焰火,踏着这似金似银的纸屑,看看这摩肩接踵的人群,我由衷的庆贺,多亏听妈的话,小时候高升、响鞭放到了点子上,才赶走了穷气,迎来了今日的美好。
如今,年龄原因,我们大多摸摸看看这些“年货”,很少伸手点燃烟花爆竹了,身份由放烟花者变为出资运输者,点火燃放的这种快乐、过瘾的美事,交给儿子,又转给了孙辈,但是,我们都怀念烟花爆竹,愿意寒风中陪看、助威、叫好。
烟花爆竹,给了我们童年的祈盼,一年一度的狂欢,温饱不足中的“富足”……